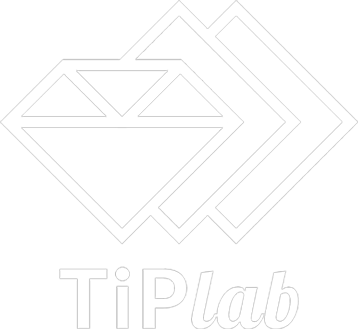根据《实施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化学仿制药申请人提交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应当对照已在中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公开的专利信息,针对被仿制药每一件相关的药品专利作出声明。声明分为四类:
一类声明:中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中没有被仿制药的相关专利信息;
二类声明:中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收录的被仿制药相关专利权已终止或者被宣告无效,或者仿制药申请人已获得专利权人相关专利实施许可;
三类声明:中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收录有被仿制药相关专利,仿制药申请人承诺在相应专利权有效期届满之前所申请的仿制药暂不上市;
四类声明:中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收录的被仿制药相关专利权应当被宣告无效,或者其仿制药未落入相关专利权保护范围。
虽然《实施办法》第六条的四种声明方式已囊括了大部分场景,但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仍有一些场景存在争议。本文,我们将结合实际案例探讨仿制药企业应对这些争议场景时,可行的专利声明方式。
场景1:声明在先登记在后的专利,仿制药企业后续是否需要修改声明
根据《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相关信息发生变化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在信息变更生效后30日内完成更新。也就是说专利信息登记平台登记的专利信息是动态的,一些在审申请和尚未来得及登记的授权专利可能在后续更新到平台上。那么,如果仿制药在递交上市许可申请的时候,因尚未有专利登记而作出了一类声明;但在仿制药获批前,原研药上市许可持有人登记了专利,仿制药企业该如何处理?
根据《实施办法》第六条规定,专利声明应以仿制药“提交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的专利登记状态为准,仿制药在申请上市时如果平台上并没有相关专利登记,仿制药上市申请人作出一类声明并没有过错。但根据“阿普米司特片案”【(2023)最高法知民终1593、1594和1595号】中最高院的观点,如果原研上市许可持有人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进行了新的专利登记,仿制药企业需要更正其专利声明。即使仿制药企业拒绝更正,原研药企仍可能有权提起确认落入之诉。
在“阿普米司特片案” 中,仿制药申请人作出一类声明时,原研药的相关专利尚未登记,相关专利(即涉案专利)在仿制药上市申请受理后的第3天才被登记在专利信息登记平台上(但满足原研药获批之后的30日内)。关于该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均认为:
在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于规定期限内正确登记专利信息,但仿制药申请人于专利信息登记前已先行作出一类声明的情况下,如果简单地以仿制药申请人提交仿制药上市许可申请时涉案专利信息尚未在专利信息登记平台中登记为由,认定仿制药申请人所作一类声明正确,并进一步认定此类案件不符合专利法第七十六条有关起诉条件的规定,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本意,会导致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与仿制药申请人之间的利益失衡,也会导致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被实质架空,难以全面实现其制度目的。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的登记和仿制药申请人的声明在各自行为作出时形式上亦均无过错可言……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有机会在合理期限内要求仿制药申请人申请变更其声明类型……如仿制药申请人申请将其一类声明变更为四类声明,或在合理期限内拒绝申请变更,或申请变更为其他错误声明,则对于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起的确认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之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实体审理。
所以,对于仿制药企业来说,递交专利声明后仍需密切监控可以登记但尚未登记的专利(申请),必要时可以提前评估其风险等级并规划应对措施,避免自己的商业化节奏被“后续登记的相关专利”打乱。
场景2:已被国知局宣告无效但仍处于行政诉讼中的相关专利该如何进行声明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无效,但专利权人提起上诉后,尚处于行政诉讼程序中的已登记专利,仿制药企业是否可以直接进行二类声明。
《实施办法》第六条规定了二类声明包括“相关专利权被宣告无效”的场景,但并未规定“被宣告无效”指的是只需要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无效程序中宣告无效即可,还是需要考虑该“宣告无效决定”是否涉及悬而未决的后续行政诉讼。
对于该争议,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芮松艳法官在《论药品专利链接民事案件的受理条件》一文中提到:“恩杂鲁胺案”的一审法院认为,二类声明规定的相关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应指涉案专利权确定的法律状态,而非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中的认定结论。在二审程序中,双方达成和解,原告撤回起诉。(作者未从公开渠道成功获取相应的裁判文书原文,未进一步核实内容)
从目前仅有的判例来看,法院可能会倾向于认为“被宣告无效”指的是专利权确定的法律状态,即不包括:无效决定尚处于行政诉讼程序中的专利。对于这类专利,仿制药企业进行三类或四类声明可能更为合理。
此外,笔者也想尝试进一步地探讨:如果仿制药企业进行了四类声明会产生什么影响?根据现有的判例,针对在这种情况下(即相关登记的专利法律状态处于无效决定后的行政诉讼阶段),若仿制药企业(被告)不请求法院进行实体审理,即使原研药上市许可持有人基于仿制药申请人的四类声明发起的确认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之诉,法院常见的处理方式为“先行裁驳,另行起诉”。例如,“盐酸鲁拉西酮片案”【(2022)最高法知民终2177号】中,最高院的认为:
对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宣告专利权无效、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审查决定尚未确定发生法律效力时的专利权,……,人民法院在审理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提起的确认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纠纷之诉时,可以参照适用侵犯专利权纠纷解释(二)第二条关于“先行裁驳、另行起诉”的规定。
……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905号案件中,本院在涉案专利权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无效、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审查决定尚未确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对确认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纠纷之诉进行实体审理,系因双方当事人均主张该案应进行实体审理,均有在涉案仿制药上市前通过诉讼解决专利纠纷的意愿。该种情形下进行实体审理,不违反侵犯专利权纠纷解释(二)第二条中“可以”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且以双方当事人均自愿承担因专利权不稳定可能对涉案争议的解决造成的后果为前提,不影响人民法院在不具备该前提时参照适用侵犯专利权纠纷解释(二)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
也就是说,如果仿制药企业不请求法院进行实体审理,法院不会去确认仿制药是否落入该法律状态不确定的专利的保护范围内,降低了仿制药上市审批进程受到该专利影响的风险。
此外,如果仿制药有足够的证据和信心证明仿制药不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围内,且在商业层面,需要在仿制药上市前诉讼解决该专利纠纷,则也可以考虑请求法院进行实体审理。但笔者想要提示的是,仿制药需要慎重衡量法院可能作出“确认落入专利保护范围”的决定,而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场景3:3类仿制药该如何进行声明
最后,我们将讨论3类仿制药(即仿制境外上市但境内未上市原研药品的药品)上市申请人该如何声明?参考“哌柏西利片案”最高院的观点,对于3类仿制药,仿制药企业需要对相同剂型的其它规格项下已登记的专利作出专利声明,但无需对不同剂型下登记的相关专利作出专利声明。
在“哌柏西利片案”【(2023)最高法知民终1233、1234号】 中,原研药企在境内仅上市了两个规格(25 mg和125 mg)的片剂以及三个规格(75 mg、100 mg和125 mg)的胶囊剂,但仿制药申请上市的为75 mg和100 mg规格的片剂。最高院认为:
专利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所称的“相关的专利”应理解为与已经在中国上市的被仿制药相对应地登记在专利信息登记平台的专利。
因哌柏西利片与哌柏西利胶囊为不同剂型的不同药物,某有限责任公司针对某制药有限公司申请注册的哌柏西利片仿制药提起确认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纠纷之诉,但涉案专利并非与已在中国上市的哌柏西利片对应登记的专利,不属于哌柏西利片“相关的专利”,故某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不符合专利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条件。(笔者注:涉案专利为已登记的哌柏西利胶囊相关专利)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一审裁定认为25mg、125mg哌柏西利片的获批并不意味着涉案75 mg哌柏西利片原研药在中国可合法上市,涉案75mg哌柏西利片原研药仍属于未在中国注册上市的药品,仿制药申请人基于此也只能作出一类声明。对此,尽管在我国现行药品管理制度中,仅存在规格差异的化学药品也需要分别进行申请注册并获得不同的批号,但同一剂型的仿制药可以使用不同规格的原研药作为参比制剂,并将与该参比制剂质量和疗效一致性的数据作为申请注册的依据。故在与被仿制药仅存在规格差异的原研药已在专利信息登记平台中登记专利的情况下,如果认定仿制药申请人只能作出一类声明,则与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实践不符,也与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兼顾原研药专利权人和仿制药申请人及社会公众利益的目的不符。因此,该种情形下,仿制药申请人原则上应对照专利信息登记平台登记的该被仿制药其他规格项下登记的相关专利作出声明。
也就是说仿制药企业在进行专利声明的时候需要考虑同剂型下不同规格的原研产品是否存在专利登记情况。不过,笔者注意到,最高院关于“仿制药申请人原则上应对照专利信息登记平台登记的该被仿制药其他规格项下登记的相关专利作出声明”的观点中,“被仿制药其他规格项”是仅指3类仿制药作为参比制剂的规格还是包括所有其它规格,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TiPLab小贴士
毕竟我国的专利链接制度从2021年实施以来时间尚短,相关规定还无法完全明确真实世界中部分复杂的实际情况该如何处理,我们也期待未来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可以最终实现该制度最初的愿景。
* 以上文字仅为促进讨论与交流,不构成法律意见或咨询建议。